孔子很少谈到利益,却赞成天命和仁德。
达巷党这个地方有人说:“孔子真伟大啊!他学问渊博,因而不能以某一方面的专长来称赞他。”孔子听说了,对他的学生说:“我要专长于哪个方面呢?驾车呢?还是射箭呢?我还是驾车吧。”
孔子说:“用麻布制成的礼帽,符合于礼的规定。现在大家都用黑丝绸制作,这样比过去节省了,我赞成大家的作法。(臣见国君)首先要在堂下跪拜,这也是符合于礼的。现在大家都到堂上跪拜,这是骄纵的表现。虽然与大家的作法不一样,我还是主张先在堂下拜。”
孔子杜绝了四种弊病:没有主观猜疑,没有定要实现的期望,没有固执己见之举,没有自私之心。
【 另一译法】
孔子一点也没有四种毛病——不凭空揣测,不绝对肯定,不拘泥固执,不唯我独是。
孔子被匡地的人们所围困时,他说:“周文王死了以后,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?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,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;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,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?”
【另一译法】
孔子被匡地的民众所拘禁。他说:“周文王既然已经不在了,一切礼乐制度、人群大道不都在我这里吗?天意若要毁灭这些,那我也就不会掌握这些。天意若未要毁灭这些,那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呀?”
太宰问子贡说:“孔夫子是位圣人吧?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?”子贡说:“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,而且使他多才多艺。”孔子听到后说:“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?我因为少年时地位低贱,所以会许多卑贱的技艺。君子会有这么多的技艺吗?不会多的。”
【另一译法】
太宰问子贡道:“孔老先生是位圣人吗?为什么这么多才多艺呢?”子贡回答说:“这是上天要让他成为圣人,又纵使他多才多艺。”
孔子听到,便道:“太宰知道我吗?我小时候穷苦,所以学会了不少鄙贱的技艺。真正的君子需要有这么多的技艺吗?不必有这么多的。”
牢说:“孔子说过,我不曾被国家所用,所以学得一些技艺。”
子牢说:“孔子说过,“我(年轻时)没有去做官,所以会许多技艺。’”
孔子说:“我有知识吗?其实没有知识。有一个乡下人问我,我对他谈的问题本来一点也不知道。我只是抓住问题的两端,这样对此问题就可以全部搞清楚了。”
孔子说:“凤鸟不来了,黄河中也不出现八卦图了。我这一生也就完了吧!”
孔子遇见穿丧服的人,当官的人和盲人时,虽然他们年轻,也一定要站起来,从他们面前经过时,一定要快步走过。
颜渊感叹地说:“(对于老师的学问与道德),我抬头仰望,越望越觉得高;我努力钻研,越钻研越觉得不可穷尽。看着它好像在前面,忽然又像在后面。老师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我,用各种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,又用各种礼节来约束我的言行,使我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,直到我用尽了我的全力。好像有一个十分高大的东西立在我前面,虽然我想要追随上去,却没有前进的路径了。”
孔子患了重病,子路派了(孔子的)门徒去作孔子的家臣(准备料理后事),后来,孔子的病好了一些,他说:“仲由很久以来就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。我明明没有家臣,却偏偏要装作有家臣,我骗谁呢?我骗上天吧?与其在家臣的侍候下死去,我宁可在你们这些学生的侍候下死去,这样不是更好吗?而且即使我不能以大夫之礼来安葬,难道就会被丢在路边没人埋吗?”
子贡说:“这里有一块美玉,是把它收藏在柜子里呢?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?”孔子说:“卖掉吧,卖掉吧!我正在等着识货的人呢。”
孔子想要搬到九夷地方去居住。有人说:“那里非常落后闭塞,不开化,怎么能住呢?”孔子说:“有君子去住,就不闭塞落后了。”
【另一更浅显译法】
孔子说想搬到九夷去住。有人说:“那地方非常简陋,怎么好住?”孔子道:“有君子住,就不简陋了。”
孔子说:“我从卫国返回到鲁国以后,乐才得到整理,雅乐和颂乐各有适当的安排。”
【另一译法】
孔子说:“我从卫国回到鲁国,才把诗的音乐[音律]整理出来,使《雅》归《雅》、《颂》归《颂》,各篇各有适当的安置。”
孔子说:“在外事奉公卿,在家孝敬父兄,有丧事不敢不尽力去办,不被酒所困,这些事对我来说有什么困难呢?”
孔子说:“我没有见过像好色那样好德的人。”
孔子说:“好比堆土成山,只要再加一筐土便成山了,如果懒得做下去,这是我自己停止的。又好比在平地上堆土成山,纵是刚刚倒下一筐土,如果决心努力前进,还是要自己坚持呵!”
孔子说:“听我说话而能毫不懈怠的,只有颜回一个人吧!”
孔子对颜渊说:“可惜呀!我只见他不断前进,从来没有看见他停止过。”
孔子说:“庄稼出了苗而不能吐穗扬花的情况是有的;吐穗扬花而不结果实的情况也有。”
【另一译法】
孔子说:“庄稼生长了,却不吐穗开花的,有过的罢!吐穗开花了,却不凝浆结实的,有过的罢!”
孔子说:“年轻人是值得敬畏的,怎么就知道后一代不如前一代呢?如果到了四五十岁时还默默无闻,那他就没有什么可以敬畏的了。”
孔子说:“符合礼法的正言规劝,谁能不听从呢?但(只有按它来)改正自己的错误才是可贵的。恭顺赞许的话,谁能听了不高兴呢?但只有认真推究它(的真伪是非),才是可贵的。只是高兴而不去分析,只是表示听从而不改正错误,(对这样的人)我拿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”
孔子说:“一国军队,可以夺去它的主帅;但一个男子汉,他的志向是不能强迫改变的。”
孔子说:“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子,与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认为是可耻的,大概只有仲由吧。(《诗经》上说:)‘不嫉妒,不贪求,为什么说不好呢?’”子路听后,反复背诵这句诗。孔子又说:“只做到这样,怎么能说够好了呢?”
孔子说:“到了寒冷的季节,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。”
孔子说:“聪明人不会迷惑,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,勇敢的人不会畏惧。”
孔子说:“可以一起学习的人,未必都能学到道;能够学到道的人,未必能够坚守道;能够坚守道的人,未必能够随机应变。”
【 另一译法】
孔子说:“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,未必可以同他一道立下高远的志向。可以同他一道立下高远的志向,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义而行事。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义而行事,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。”
古代有一首诗这样写道:“唐棣的花朵啊,翩翩地摇摆。我岂能不想念你吗?只是由于家住的地方太远了。”孔子说:“他还是没有真的想念,如果真的想念,有什么遥远呢。
罕:稀少,很少。
与:赞同、肯定。
达巷党人:古代五百家为一党,达巷是党名。这是说达巷党这地方的人。
博学而无所成名:学问渊博,因而不能以某一方面来称道他。孔子博学,而融会成体,如八音和为一乐,不得仍以八音之一名之。
吾何执:执,专执也。孔子闻党人之称美,自谦我将何执,射与御,皆属一艺,而御较卑。古人常为尊长御车,其职若为人下。又以较射择士,擅射则为人上。故孔子谦言若我能专执一艺而成名,则宜于执御也。
麻冕:麻布制成的礼帽。
纯:丝绸,黑色的丝。
俭:俭省,麻冕费工,用丝则俭省。
拜下:大臣面见君主前,先在堂下跪拜,再到堂上跪拜。
泰:这里指骄纵、傲慢。
意:同臆,猜想、猜疑。
必:必定。
固:固执己见。
我:这里指自私之心。
畏于匡:匡,地名,在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。畏,受到威胁。公元前496年,孔子从卫国到陈国去经过匡地。匡人曾受到鲁国阳虎的掠夺和残杀。孔子的相貌与阳虎相像,匡人误以孔子就是阳虎,所以将他围困。
文王:周文王,姓姬名昌,西周开国之君周武王的父亲,是孔子认为的古代圣贤之一。
兹:这里,指孔子自己。
后死者:孔子这里指自己。
与:同“举”,这里是掌握的意思。
如予何:奈我何,把我怎么样。
太宰:官名,掌握国君宫廷事务。这里的太宰,有人说是吴国的太宰伯,但不能确认。
纵:让,使,不加限量。
鄙事:卑贱的事情。
鄙夫:孔子称乡下人、社会下层的人。
空空如也:指孔子自己心中空空无知。
叩:叩问、询问。
两端:两头,指正反、始终、上下方面。
竭:穷尽、尽力追究。
凤鸟: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。传说凤鸟在舜和周文王时代都出现过,它的出现象征着“圣王”将要出世。
河不出图:传说在上古伏羲氏时代,黄河中有龙马背负八卦图而出。它的出现也象征着“圣王”将要出世。
齐衰(zī cuī):丧服,古时用麻布制成。
冕衣裳者:冕,官帽;衣,上衣;裳,下服,这里统指官服。冕衣裳者指贵族。
瞽(gǔ):盲。
少:年少。
作:站起来,表示敬意。
趋:快步走,表示敬意。
喟:音kuì,叹息的样子。
弥:更加,越发。
钻:钻研。
瞻:音zhān,视、看。
循循然善诱人:循循然,有次序地。诱,劝导,引导。
卓尔:高大、超群的样子。
末由:末,无、没有。由,途径,路径。这里是没有办法的意思。
为臣:臣,指家臣,总管。孔子当时不是大夫,没有家臣,但子路叫门人充当孔子的家臣,准备由此人负责总管安葬孔子之事。
病间:病情减轻。
无宁:宁可。“无”是发语词,没有意义。
大葬:指大夫的葬礼。
韫匵(yùn dú):收藏物件的柜子。
善贾:识货的商人。
沽:卖出去。
九夷:中国古代对于东方少数民族的通称。
陋:鄙野,文化闭塞,不开化。
自卫反鲁:公元前484年(鲁哀公十一年)冬,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,结束了14年游历不定的生活。
乐正:调整乐曲的篇章。
雅颂:这是《经》中两类不同的诗的名称。也是指雅乐、颂乐等乐曲名称。
雅颂各得其所:诗篇之分雅颂以体制,乐之分雅颂则以音律。正其乐章,如鹿鸣奏于乡饮酒、乡射、燕礼。清庙奏于祀文王、大尝禘、天子养老、两君相见之类。正其乐音,正其音律之错乱。
言此数事,于我无难。或说:孔子幼孤,其兄亦早亡,此章未必在早年,则不专为己发。要之是日常庸行,所指愈卑,用意愈切,固人人当以反省。
本章叹时人之薄于德而厚于色。或说:好色出于诚,人之好德,每不如好色之诚。又说:《史记》:“孔子居卫,灵公与夫人同车,使孔子为次乘,招摇市过之”,故有此言。
惰,懈怠义。本章承上章。然读者易于重视不惰二字,而忽了语之二字。盖答问多因其所疑,语则教其所未至。闻所语而不得于心,故惰。独颜子于孔子之言,触类旁通,心解力行,自然不懈。此见颜子之高。:
子谓颜回句断,下曰字自为一句。本章乃颜渊既死而孔子惜之之辞。进止二字与上为山章同义。:
秀:稻、麦等庄稼吐穗扬花叫秀。
后生可畏:后生,指年少者,因其来日方长,前途无限,故可畏。
焉知来者之不如今:来者,今日之后生。今,今日之成人。就目前言,似后生不如成人。然他年后生长成,焉知其必不如今日之成人乎?后来居上,出类拔萃者,亦可有之。
四十五十而无闻:无闻有两解:一,无声闻于世。一,谓其无闻于道。今从前解。古人四十曰强仕,五十而爵,四十五十,乃德立名彰之时,故孔子据以为说。
法语之言:法,指礼仪规则。这里指以礼法规则正言规劝。
巽与之言:巽,恭顺,谦逊。与,称许,赞许。这里指恭顺赞许的话。
说:同“悦”。
绎:原义为“抽丝”,这里指推究,追求,分析,鉴别。
末:没有。
三军:12500人为一军,三军包括大国所有的军队。此处言其多。
匹夫:平民百姓,主要指男子。
衣:穿,当动词用。
敝缊(yùn)袍:敝,坏。缊,旧的丝棉絮。这里指破旧的丝棉袍。
狐貉:用狐和貉的皮做的裘皮衣服。
不忮(zhì)不求,何用不臧:这两句见《诗经•邶风•雄雉》篇。忮,害,嫉妒。臧,善,好。
凋,凋伤义。凋在众木之后,曰后凋。春夏之交,众木茂盛,及至岁寒,尽归枯零。独有松柏,支持残局,重待阳和,所谓士穷见节义,世乱识忠臣。然松柏亦非不凋,但其凋在后,旧叶未谢,新叶已萌,虽凋若不凋。道之将废,虽圣贤不能回天而易命,然能守道,不与时俗同流,则其绪有传,其风有继。本章只一语,而义喻无穷,至今通俗皆知,诗人运用此章义者尤广。吾中华文化之历久常新,孔子此章所昭示,其影响尤为不小。:
知者不惑:知者明道达义,故能不为事物所惑。
仁者不忧:仁者悲天悯人,其心浑然与物同体,常能先天下之忧而忧,然其为忧,侧怛广大,无私虑私忧。
勇者不惧:勇者见义勇为,志道直前。
适道:适,往。这里是志于道,追求道的意思。
立:坚持道而不变。
权:秤锤。这里引申为权衡轻重。
唐棣:一种植物,属蔷薇科,落叶灌木。
偏其反而:形容花摇动的样子。
室是远而:只是住的地方太远了。
唐棣之华,偏其反而:棣花有赤白两种,树高七八尺,其花初开相反,终乃合并。实大如李,六月中熟,可食。唐棣白色,华即花字。偏亦作翩,反或说当与翻同。翩翻,花摇动貌。
岂不尔思,室是远而:棣花翩翻摇动,似有情,实无情。诗人借以起兴,言我心摇摇,亦如棣花翩翻,非不相念于尔,但居室远隔,不易常亲耳。上四句是逸诗。
未之思也。夫何远之有:孔子引此逸诗而说之,谓实不思而已。若果思之,即近在我心,何远之有。
“子罕言利”,说明孔子对“利”的轻视。在《论语》书中,我们也多处见到他谈“利”的问题,但基本上主张“先义后利”、“重义轻利”,可以说孔子很少谈“利”。此外,本章说孔子赞同“命”和“仁”,表明孔子对此是十分重视的。孔子讲“命”,常将“命”与“天”相连,即“天命”,这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孔子还讲“仁”,这里其思想的核心。对此,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也已评论,请参阅。
对于本章里“博学而无所成名一句”的解释还有一种,即“学问广博,可惜没有一艺之长以成名。”持此说的人认为,孔子表面上伟大,但实际上算不上博学多识,他什么都懂,什么都不精。对此说,我们觉得似乎有些求全责备之嫌了。
孔子赞同用比较俭省的黑绸帽代替用麻织的帽子这样一种作法,但反对在面君时只在堂上跪拜的作法,表明孔子不是顽固地坚持一切都要合乎于周礼的规定,而是在他认为的原则问题上坚持己见,不愿作出让步,因跪拜问题涉及“君主之防”的大问题,与戴帽子有根本的区别。
本章是孔子的弟子们对孔子日常言行态度等的一个概括。要用一句话概括孔子也很难,此处只从反面描述了孔子所没有的、常人所常有的四种毛病。
“绝四”是孔子的一大特点,这涉及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。人只有首先做到这几点才可以完善道德,修养高尚的人格。
外出游说时被围困,这对孔子来讲已不是第一次,当然这次是误会。但孔子有自己坚定的信念,他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,认为自己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。不过,当孔子屡遭困厄时,他也感到人力的局限性,而把决定作用归之于天,表明他对“天命”的认可。
作为孔子的学生,子贡认为自己的老师是天才,是上天赋予他多才多艺的。但孔子这里否认了这一点。他说自己少年低贱,要谋生,就要多掌握一些技艺,这表明,当时孔子并不承认自己是圣人。
孔子本人并不是高傲自大的人。事实也是如此。人不可能对世间所有事情都十分精通,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。但孔子有一个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,这就是“叩其两端而竭”,只要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,就能求得问题的解决。这种方法,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,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思想方法。
孔子为了恢复礼制而辛苦奔波了一生。到了晚年,他看到周礼的恢复似乎已经成为泡影,于是发出了以上的哀叹。从这几句话来看,孔子到了晚年,他头脑中的宗教迷信思想比以前更为严重。
孔子对于周礼十分熟悉,他知道遇到什么人该行什么礼,对于尊贵者、家有丧事者和盲者,都应礼貌待之。孔子之所以这样做,也说明他极其尊崇“礼”,并尽量身体力行,以恢复礼治的理想社会。
本章描述的场景,大概是孔子时代的一些日常礼仪,或者是孔子发明的,或者是古礼相传。中国是礼仪之邦,全国各地对于丧者及居丧者都有着不同的讲究、礼节,而儒家思想中,对于丧礼亦蕴含着教化民众之功效。
儒家敬重死者(瞽者无目无视,亦乃不幸之人也。),亦敬重居丧者之家人。其实何必是儒家,即如是人,岂不均应于此?人家家里失去了亲人,心中之哀戚多矣,我见之,坐而起之,过之,改步疾行,既体现了对死者之敬重,亦乃对于生者的敬重,于默默无闻间、不经意之处,给居丧者的心里送去一丝人文之温暖,这世界岂不更加温馨。
颜渊在本章里极力推崇自己的老师,把孔子的学问与道德说成是高不可攀。此外,他还谈到孔子对学生的教育方法,“循循善诱”则成为日后为人师者所遵循的原则之一。
本章记颜子赞叹孔子之道之高且深,而颜子之好学,所以得为孔门最高弟子,亦于此见矣。惟孔子之道,虽极高深,若为不可几及,亦不过在人性情之间,动容之际,饮食起居交接应酬之务,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常,出处去就辞受取舍,以至政事之设施,礼乐文章之讲贯。细读《论语》,孔子之道,尽在其中,所谓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。非舍具体可见之外,别有一种不可测想推论之道,使人无从窥寻。学者熟读《论语》,可见孔子之道,实平易而近人。而细玩此章,可知即在此平易近人之中,而自有其高深不可及处。虽以颜子之贤,而犹有此叹。今欲追寻孔子之道,亦惟于博文约礼,欲罢不能中,逐步向前,庶几达于颜子所叹欲从末由之一境,则已面对孔子之道之极高峻绝处。若舍其平实,而索之冥漠,不务于博文约礼,而别作仰钻,则未为善读此章。
儒家对于葬礼十分重视,尤其重视葬礼的等级规定。对于死去的人,要严格地按照周礼的有关规定加以埋葬。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安葬仪式,违反了这种规定,就是大逆不道。孔子反对学生们按大夫之礼为他办理丧事,是为了恪守周礼的规定。
“待贾而沽”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,孔子自称是“待贾者”,他一方面四处游说,以宣传礼治天下为己任,期待着各国统治者能够行他之道于天下;另一方面,他也随时准备把自己推上治国之位,依靠政权的力量去推行礼。因此,本章反映了孔子求仕的心理。
本章子贡以孔子怀道不仕,故设此问。孔子重言沽之,则无不仕之心可知。盖孔子与子贡之分别,在求字与待字上。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,若有求无待,则将炫之,与藏之相异。
中国古代,中原地区的人把居住在东面的人们称为夷人,认为此地闭塞落后,当地人也愚昧不开化。孔子在回答某人的问题时说,只要有君子去这些地方住,传播文化知识,开化人们的愚蒙,那么这些地方就不会闭塞落后了。
孔子对诗经可不是简单的整理,仅从篇幅上看,就可以看出其对诗经所做的工作了,三千多篇,被孔子运用春秋笔法,删减到三百零五篇,这工作亦如其笔削春秋。
“出则事公卿”,是为国尽忠;“入则事父兄”,是为长辈尽孝。忠与孝是孔子特别强调的两个道德规范。它是对所有人的要求,而孔子本人就是这方面的身体力行者。在这里,孔子说自己已经基本上做到了这几点。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:“(孔子)居卫月馀,灵公与夫人同车,宦者雍渠参乘,出,使孔子为次乘,招摇市过之。孔子曰:‘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’”于是,去卫,过曹。则孔子之所以有此感叹,发生在周游列国期间,在卫国时因为卫灵公而发,而涵盖普罗大众,又因见卫灵公之好色过于好德,“丑之”(以之为丑),离开了卫国。如此,孔子之叹,用意显矣:好德未如好色,常人也;好色未如好德,圣人也;卫灵公好德未如好色,孔子“丑之”、去之。卫灵公这样的人,孔子不和他玩。
孔子的学生颜渊是一个十分勤奋刻苦的人,他在生活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要求,而是一心用在学问和道德修养方面。但他却不幸死了。对于他的死,孔子自然十分悲痛。他经常以颜渊为榜样要求其他学生。
这是孔子以庄稼的生长、开花到结果来比喻一个人从求学到做官的过程。有的人很有前途,但不能坚持始终,最终达不到目的。在这里,孔子还是希望他的学生既能勤奋学习,最终又能做官出仕。
这就是说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,“长江后浪推前浪,一代更比一代强”。社会在发展,人类在前进,后代一定会超过前人,这种今胜于昔的观念是正确的,说明孔子的思想并不完全是顽固守旧的。
这里讲的第一层意见是言行一致的问题。听从那些符合礼法的话只是问题的一方面,而真正依照礼法的规定去改正自己的错误,才是问题的实质。第二层的意思是忠言逆耳,而顺耳之言的是非真伪,则应加以仔细辨别。对于孔子所讲的这两点,我们今天还应借鉴它,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办事。
“理想”这个词,在孔子时代称为“志”,就是人的志向、志气。“匹夫不可夺志”,反映出孔子对于“志”的高度重视,甚至将它与三军之帅相比。对于一个人来讲,他有自己的独立人格,任何人都无权侵犯。作为个人,他应维护自己的尊严,不受威胁利诱,始终保持自己的“志向”。这就是中国人“人格”观念的形成及确定。
这一章记述了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先夸奖又批评的两段话。他希望子路不要满足于目前已经达到的水平,因为仅是不贪求、不嫉妒是不够的,还要有更高的更远的志向,成就一番大事业。
孔子认为,人是要有骨气的。作为有远大志向的君子,他就像松柏那样,不会随波逐流,而且能够经受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。孔子的话,语言简洁,寓意深刻,值得我们深入思考。
在儒家传统道德中,智、仁、勇是重要的三个范畴。《礼记•中庸》说:“知、仁、勇,三者天下之达德也。”孔子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具备这三德,成为真正的君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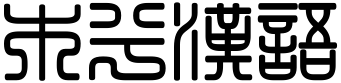
本篇共包括31章。其中著名的文句有:“出则事公卿,入则事父兄”;“后生可畏,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”;“三军可夺帅,匹夫不可夺志也”;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”;“知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”。本篇涉及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;孔子弟子对其师的议论;此外,还记述了孔子的某些活动。
这一章与上一章的内容相关联,同样用来说明孔子「我非生而知之」的思想。他不认为自己是「圣人」,也不承认自己是「天才」,他说他的多才多艺是由于年轻时没有去做官,生活比较清贫,所以掌握了这许多的谋生技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