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说:“只阐述而不创作,相信而且喜好古代的东西,我私下把自己比做老彭。”
孔子说:“默默地记住(所学的知识),学习不觉得厌烦,教人不知道疲倦,这对我能有什么困难呢?”
孔子说:“(许多人)对品德不去修养,学问不去讲求,听到义不能去做,有了不善的事不能改正,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事情。”
孔子闲居在家里的时候,衣冠楚楚,仪态温和舒畅,悠闲自在。
孔子说:“我衰老得很厉害了,我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。”
孔子说:“以道为志向,以德为根据,以仁为凭藉,活动于(礼、乐等)六艺的范围之中。”
孔子说:“只要自愿拿着十馀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,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。”
孔子说:“教导学生,不到他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,不去开导他;不到他想出来却说不出来的时候,不去启发他。教给他一个方面的东西,他却不能由此而推知其他三个方面的东西,那就不再教他了。”
孔子在有丧者之侧进食,从未饱过。
【另一译法】孔子在死了亲属的人旁边吃饭,不曾吃饱过。
孔子哪天吊丧哭了,当天即不再歌唱。
先生告颜渊说:“有用我的,则将此道行于世。不能有用我的,则将此道藏于身。只我与你能这样了。”子路说:“老师倘有行三军之事,将和谁同事呀?”孔子说:“徒手搏虎,徒身涉河,死了也不追悔的人,我是不和他同事的。定要临事能小心,好谋始作决定的人,我才和他同事吧。”
孔子说:“如果富贵合乎于道就可以去追求,虽然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,我也愿意去做。如果富贵不合于道就不必去追求,那就还是按我的爱好去干事。”
孔子平常谨慎的有三件事:一斋戒,二战阵,三疾病。
孔子在齐国听到了《韶》乐,有很长时间尝不出肉的滋味,他说,“想不到《韶》乐的美达到了这样迷人的地步。”
冉有(问子贡)说:“老师会帮助卫国的国君吗?”子贡说:“嗯,我去问他。”于是就进去问孔子:“伯夷、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呢?”(孔子)说:“古代的贤人。”(子贡又)问:“他们有怨恨吗?”(孔子)说:“他们求仁而得到了仁,为什么又怨恨呢?”(子贡)出来(对冉有)说:“老师不会帮助卫君。”
孔子说:“吃粗粮,喝白水,弯着胳膊当枕头,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。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,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。”
孔子说:“再给我几年时间,到五十岁学习《易》,我便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。”
孔子有时讲雅言,读《诗》、念《书》、赞礼时,用的都是雅言。
叶公向子路问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,子路不答。孔子(对子路)说:“你为什么不样说,他这个人,发愤用功,连吃饭都忘了,快乐得把一切忧虑都忘了,连自己快要老了都不知道,如此而已。”
孔子说:“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,而是爱好古代的东西,勤奋敏捷地去求得知识的人。”
孔子不谈论怪异、暴力、变乱、鬼神。
孔子说:“三个人一起走路,其中必定有人可以作我的老师。我选择他善的品德向他学习,看到他不善的地方就作为借鉴,改掉自己的缺点。”
孔子说:“上天把德赋予了我,桓魋能把我怎么样?”
孔子说:“学生们,你们以为我对你们有什么隐瞒的吗?我是丝毫没有隐瞒的。我没有什么事不是和你们一起干的。我孔丘就是这样的人。”
孔子以文、行、忠、信四项内容教授学生。
【另一译法】
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:历代文献,社会生活的实践,对待别人的忠心,与人交际的信实。
孔子说:“圣人我是不可能看到了,能看到君子,这就可以了。”孔子又说:“善人我不可能看到了,能见到始终如一(保持好的品德的)人,这也就可以了。没有却装作有,空虚却装作充实,穷困却装作富足,这样的人是难于有恒心(保持好的品德)的。”
孔子只用(有一个鱼钩)的钓竿钓鱼,而不用(有许多鱼钩的)大绳钓鱼。只射飞鸟,不射巢中歇宿的鸟。
孔子说:“有这样一种人,可能他什么都不懂却在那里凭空创造,我却没有这样做过。多听,选择其中好的来学习;多看,然后记在心里,这是次一等的智慧。”
(孔子认为)很难与互乡那个地方的人谈话,但互乡的一个童子却受到了孔子的接见,学生们都感到迷惑不解。孔子说:“我是肯定他的进步,不是肯定他的倒退。何必做得太过分呢?人家改正了错误以求进步,我们肯定他改正错误,不要死抓住他的过去不放。”
孔子说:“仁难道离我们很远吗?只要我想达到仁,仁就来了。”
陈司败问:“鲁昭公懂得礼吗?”孔子说:“懂得礼。”孔子出来后,陈司败向巫马其作了个揖,请他走近自己,对他说:“我听说,君子是没有偏私的,难道君子还包庇别人吗?鲁君在吴国娶了一个同姓的女子为做夫人,是国君的同姓,称她为吴孟子。如果鲁君算是知礼,还有谁不知礼呢?”巫马期把这句话告诉了孔子。孔子说:“我真是幸运。如果有错,人家一定会知道。”
孔子与别人一起唱歌,如果唱得好,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,然后和他一起唱。
孔子说:“就书本知识来说,大约我和别人差不多,做一个身体力行的君子,那我还没有做到。”
孔子说:“如果说到圣与仁,那我怎么敢当!不过(向圣与仁的方向)努力而不感厌烦地做,教诲别人也从不感觉疲倦,则可以这样说的。”公西华说:“这正是我们学不到的。”
孔子病情严重,子路向鬼神祈祷。孔子说:“有这回事吗?”子路说:“有的。《诔》文上说:‘为你向天地神灵祈祷。’”孔子说:“我很久以来就在祈祷了。”
孔子说:“奢侈了就会越礼,节俭了就会寒酸。与其越礼,宁可寒酸。 ”
孔子说:“君子心胸宽广,小人经常忧愁。”
孔子温和而又严厉,威严而不凶猛,庄重而又安祥。
述而不作:述,传述。作,创造。
窃:私,私自,私下。
老彭:人名,但究竟指谁,学术界说法不一。有的说是殷商时代一位“好述古事”的“贤大夫”;有的说是老子和彭祖两个人,有的说是殷商时代的彭祖。
识(zhì):记住的意思。
诲:教诲。
何有于我哉:对我有什么难呢?
徙:迁移。此处指靠近义、做到义。
燕居:安居、家居、闲居。
申申:衣冠整洁。
夭夭:行动迟缓、斯文和舒和的样子。
周公:姓姬名旦,周文王的儿子,周武王的弟弟,成王的叔父,鲁国国君的始祖,传说是西周典章制度的制定者,他是孔子所崇拜的所谓“圣人”之一。
德:旧注云:德者,得也。能把道贯彻到自己心中而不失掉就叫德。
艺:艺指孔子教授学生的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等六艺,都是日常所用。
束修(xiū):修,干肉,又叫脯。束修就是十条干肉。孔子要求他的学生,初次见面时要拿十馀干肉作为学费。后来,就把学生送给老师的学费叫做“束修”。
愤:苦思冥想而仍然领会不了的样子。
悱(fěi):想说又不能明确说出来的样子。
隅(yú):角落。
用之则行,舍之则藏:有用我者,则行此道于世。不能有用我者,则藏此道在身。舍同舍。即不用义。
唯我与尔有是夫:尔指颜渊。身无道,则用之无可行,舍之无可藏。用舍在外,行藏在我。孔子之许颜渊,正许其有此可行可藏之道在身。有是夫是字,即指此道。有此道,始有所谓行藏。
子行三军则谁与:凡从学于孔门者,莫不有用世之才,亦莫不有用世之志。子路自审不如颜渊,而行军乃其所长,故以问。古制,大国三军,则非粗勇之所胜任可知。
暴虎冯河:暴虎,徒手搏之。冯河,徒身涉之。此皆粗勇无谋,孔子特设为譬喻,非谓子路实有此。
临事而惧,好谋而成:成,定义。临事能惧,好谋始定。用舍不在我,我可以不问。行军不能必胜而无败,胜败亦不尽在我,然我不可以不问。惧而好谋,是亦尽其在我而已。子路勇于行,谓行三军,己所胜任。不知行三军尤当慎,非曰用之则行而已。孔子非不许其能行三军,然惧而好谋,子路或有所不逮,故复深一步教之。
富:指升官发财。
求:指合于道,可以去求。
执鞭之士:古代为天子、诸侯和官员出入时手执皮鞭开路的人。意思指地位低下的职事。
慎:不轻视,不怯对。
齐(zhaī):通「斋」。古人祭前之斋,变食迁坐,齐其思虑之不齐,将以交神明。子曰:「我不与祭,如不祭。」若于斋不慎,则亦祭如不祭矣。
战:众之死生所关,故必慎。
疾:吾身生死所关,故必慎。
此章亦言道命。神明战争疾病三者,皆有不可知,则亦皆有命。慎处其所不可知,即是道。孔子未尝屡临战事,则此章殆亦孔子平日之言。:
《韶》:舜时古乐曲名。
为:这里是帮助的意思。
卫君:卫出公辄,是卫灵公的孙子。公元前492年 ̄前481年在位。他的父亲因谋杀南子而被卫灵公驱逐出国。灵公死后,辄被立为国君,其父回国与他争位。
诺:答应的说法。
饭疏食,饭,这里是“吃”的意思,作动词。疏食即粗粮。:
曲肱(gōng):胳膊,由肩至肘的部位。曲肱,即弯着胳膊。
加:这里通“假”字,给予的意思。
易:指《周易》,古代占卜用的一部书。
雅言:周王朝的京畿之地在今陕西地区,以陕西语音为标准音的周王朝的官话,在当时被称作“雅言”。孔子平时谈话时用鲁国的方言,但在诵读《诗》、《书》和赞礼时,则以当时陕西语音为准。
叶(shè)公:叶公姓沈名诸梁,楚国的大夫,封地在叶城(今河南叶县南),所以叫叶公。
云尔:云,代词,如此的意思。尔同耳,而已,罢了。
非生而知之:时人必有以孔子为生知,故孔子直言其非。
好古:好学必好古。若世无古今,人生限在百年中,亦将无学可言。孔子之学,特重人文,尤必从古史经验前言往行中得之,故以好古自述己学。
敏以求之:敏,勤捷义,犹称汲汲。此章两之字,其义何指,尤须细玩。
桓魋(tuí):任宋国主管军事行政的官——司马,是宋桓公的后代。
二三子:这里指孔子的学生们。
文:文献、古籍等。
行:指德行,也指社会实践方面的内容。
忠:尽己之谓忠,对人尽心竭力的意思。
信:以实之谓信。诚实的意思。
斯:就。
恒:指恒心。
约:穷困。
泰:这里是奢侈的意思。
圣人君子以学言,善人有恒以质言。亡,通无。时世浇漓,人尚夸浮,匿无为有,掩虚为盈,心困约而外示安泰,乃难有恒。人若有恒,三人行,必可有我师,积久为善人矣。善人不践迹,若能博文好古,斯即为君子。君子学之不止,斯为圣人。有恒之与圣人,相去若远,然非有恒,无以至圣。章末申言无恒之源,所以诫人,而开示其入德之门。:
本章两子曰,或说当分两章,或说下子曰二字衍文。今按:两子曰以下,所指稍异,或所言非出一时,而意则相足,子曰字非衍,亦不必分章为是。
又按:当孔子时,圣人固不易得见,岂遂无君子善人与有恒者?所以云然者,以其少而思见之切。及其既见,则悦而进之,如曰“君子哉若人”是也。凡此类,当得意而忘言,不贵拘文而曲说。
纲:大绳。这里作动词用。在水面上拉一根大绳,在大绳上系许多鱼钩来钓鱼,叫纲。
弋:用带绳子的箭来射鸟。
宿:指归巢歇宿的鸟儿。
不知而作:此作字或解著作,然孔子时,尚无私家著作之风。或解作为,所指太泛,世之不知而作者多矣,不当用盖有二字。此作字当同述而不作之作,盖指创制立说言。
多见而识之:识,记义。闻指远。古人之嘉言懿行,良法美制,择而从之,谓传述。见指近,当身所见,是非善恶,默识在心,备参究。
知之次也:作者之圣,必有创新,为古今人所未及。多闻多见,择善默识,此皆世所已有,人所已知,非有新创,然亦知之次。知者谓知道。若夫不知妄作,自谓之道,则孔子无之。
此章非孔子之自谦。孔子立言明道,但非不知而作。所谓“我非生而知之,好古敏以求之。”是孔子已自承知之。又曰:“温故而知新,可以为师矣。”孔子以师道自居,则决非仅属多闻多见之知可知。本章上半节,乃孔子之自述。下半节,则指示学者以从入之门。
互乡:地名,具体所在已无可考。
与:赞许。
进、退:一说进步、退步;一说进见请教,退出以后的作为。
洁己:洁身自好,努力修养,成为有德之人。
不保其往:保,一说担保,一说保守。往,一说过去,一说将来。
互乡难与言:互乡,乡名。其乡风俗恶,难与言善。或说:不能谓一乡之人皆难与言,章首八字当通为一句。然就其风俗而大略言之,亦何不可。若八字连为一句,于文法不顺惬,今不从。
门人惑:门人不解孔子何以见此互乡童子。
与其进也,不与其退也:与,赞可义。童子进请益,当予以同情,非即同情及其退后之如何。
唯何甚:甚,过分义。谓如此有何过分。孟子曰:“仲尼不为已甚”,即此甚字义。
人洁己以进:洁,清除污秽义。童子求见,当下必有一番洁身自好之心矣。
不保其往也:保,保任义,犹今言担保。往字有两解。一说指已往。一说指往后。后说与不与其退重复,当依前说。或疑保字当指将来,然云不保证其已往,今亦有此语。或又疑本章有错简,当云与其洁不保其往,与其进不与其退始是。今按:与其进,不与其退,始为凡有求见者言。与其洁,不保其往,此为其人先有不洁者言。乃又进一层言之,似非错简。
仁道出于人心,故反诸己而即得。仁心仁道皆不远人,故我欲仁,斯仁至。惟求在己成德,在世成道,则难。故孔子极言仁之易求,又极言仁之难达。此处至字,即日月至焉之至,当与彼章参读。:
陈司败:陈国主管司法的官,姓名不详,也有人说是齐国大夫,姓陈名司败。
昭公:鲁国的君主,名惆,公元前541-前510年在位。“昭”是谥号。
揖:做揖,行拱手礼。
巫马期:姓巫马名施,字子期,孔子的学生,比孔子小30岁。
党:偏袒、包庇的意思。
取:同娶。
为同姓:鲁国和吴国的国君同姓姬。周礼规定:同姓不婚,昭公娶同姓女,是违礼的行为。
吴孟子:鲁昭公夫人。春秋时代,国君夫人的称号,一般是她出生的国名加上她的姓,但因她姓姬,故称为吴孟子,而不称吴姬。
反,复义。本章见孔子之爱好音乐,又见其乐取于人以为善之美德。遇人歌善,必使其重复再歌,细听其妙处,再与之相和而歌。:
莫:约摸、大概、差不多。
文莫:有两义,乃忞(mǐn ,wěn,mín) 慔(mù)之假借。《说文》:忞,强也。慔(mù),勉也。忞读若妟(yàn?),妟莫双声,犹言黾(mǐn)勉,乃努力义。一说以文字断句,莫作疑辞。谓文或犹人,行则不逮。两说均通,但疑孔子决不如此自谦。今从前解。
抑:折的语气词,“只不过是”的意思。
为之:指圣与仁。
云尔:这样说。
圣与仁:圣智古通称。此孔子自谦,谓圣智与仁德,吾不敢当。盖当时有称孔子圣且仁者,故为此谦辞。
为之不厌,诲人不倦:此之字即指圣与仁之道言。为之不厌,谓求知与仁努力不懈。亦即以所求不倦诲人。
可谓云尔:云尔,犹云如此说,即指上文不厌不倦言。
正唯弟子不能学也:正唯犹言正在这上,亦指不厌不倦。
疾病:疾指有病,病指病情严重。
请祷:向鬼神请求和祷告,即祈祷。
有诸:诸,“之于”的合音。意为:有这样的事吗。
诔(lěi):祈祷文。
神祇(qí):古代称天神为神,地神为祇。
有之乎,问辞。或说:有此事否?病而祷于鬼神,古今礼俗皆然,孔子何为问此?或说:有此理否?孔子似亦不直斥祷神为非理。此语应是问有代祷之事是否。如周公金滕,即代祷也,然未尝先告武王,又命祝史使不敢言。今子路以此为请,故孔子问之。
诔曰:诔一本作讄(lěi),当从之。讄,施于生者,累其功德以求福。诔,施于死者,哀其死,述行以谥之。
祷尔于上下神祗:子路引此讄词也。上下谓天地,神属天,祗属地。尔训汝。祷尔于三字,即别人代祷之辞,故子路引此以答。
丘之祷久矣:孔子谓我日常言行,无不如祷神求福,素行合于神明,故曰祷久矣,则无烦别人代祷。
孙:同逊,恭顺。不孙,即为不顺,这里的意思是“越礼”。
固:简陋、鄙陋。这里是寒酸的意思。
奢者常欲胜于人。孙字又作逊,不逊,不让不顺义。固,固陋义。务求于俭,事事不欲与人通往来,易陷于固陋。二者均失,但固陋病在己,不逊则陵人。孔子重仁道,故谓不逊之失更大。:
坦荡荡:心胸宽广、开阔、容忍。
长戚戚:经常忧愁、烦恼的样子。
坦,平也。荡荡,宽广貌。君子乐天知命,俯仰无愧,其心坦然,荡荡宽大。戚戚,蹙缩貌,亦忧惧义。小人心有私,又多欲,驰竞于荣利,耿耿于得丧,故常若有压迫,多忧惧。本章分别君子小人,单指其心地与气貌言。读者常以此反省,可以进德。:
温,和顺义。厉,严肃貌。厉近有威,温近不猛。恭常易近于不安。孔子修中和之德,即在气貌之间,而可以窥其心地修养之所至。学者当内外交修,即从外面气貌上,亦可验自己之心德。:
在这一章里,孔子提出了“述而不作”的原则,这反映了孔子思想上保守的一面。完全遵从“述而不作”的原则,那么对古代的东西只能陈陈相因,就不再会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。这种思想在汉代以后开始形成古文经学派,“述而不作”的治学方式,对于中国人的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局限作用。
这一章紧接前一章的内容,继续谈论治学的方法问题。前面说他本人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”,此章则说他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;反映了孔子教育方法的一个侧面。这对中国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以至于在今天,我们仍在宣传他的这一教育学说。
春秋末年,天下大乱。孔子慨叹世人不能自见其过而自责,对此,他万分忧虑。他把道德修养、读书学习和知错即改三个方面的问题相提并论,在他看来,三者之间也有内在联系,因为进行道德修养和学习各种知识,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及时改正自己的过失或“不善”,只有这样,修养才可以完善,知识才可以丰富。
周公是中国古代的“圣人”之一,孔子自称他继承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道统,肩负着光大古代文化的重任。这句话,表明了孔子对周公的崇敬和思念,也反映了他对周礼的崇拜和拥护。
《礼记•学记》曾说:“不兴其艺,不能乐学。故君子之于学也,藏焉,修焉,息焉,游焉。夫然,故安其学而亲其师,乐其及而信其道,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。”这个解释阐明了这里所谓的“游于艺”的意思。孔子培养学生,就是以仁、德为纲领,以六艺为基本,使学生能够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。
这一章中孔子所说的这段话,表明了他诲人不倦的精神,也反映了他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思想。过去有人说,既然要交十束干肉作学费,那必定是中等以上的人家之子弟才有入学的可能,贫穷人家自然是交不出十束干肉来的,所以孔子的“有教无类”只停留在口头上,在社会实践中根本不可能推行。用这种推论否定孔子的“有教无类”的教育思想,过于理想化和幼稚。在任何社会里,要做到完全彻底的有教无类,恐怕都有相当难度,这要归之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。
在《雍也》一篇第21章中,孔子说:“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;中人以下,不可以语上也。”这一章继续谈他的教育方法问题。在这里,他提出了“启发式”教学的思想。从教学方面而言,他反对“填鸭式”、“满堂灌”的作法。要求学生能够“举一反三”,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,再对他们进行启发、开导,这是符合教学基本规律的,而且具有深远的影响,在今天教学过程中仍可以加以借鉴。
为什么会这样?
丧者,是指有亲属刚刚去世,其心必哀戚,甚至吃不下饭去,孔子在他旁边吃饭,自感于我心有戚戚焉,恻隐之心一动,饭就吃不饱了。
哭,指吊丧。如今城市死了人,往往开个追悼会,亲朋好友戴朵白花,在死者的遗体前来个三鞠躬,死者就被拉走火化了,仪式非常简单。在古代,可不这样,儒家提倡“丧尽礼, 祭尽诚,事死者,如事生。”(《弟子规》)人死之后,亲朋好友要到死者家中吊丧,今日之农村,此风俗依旧,如我的老家聊城,孝子们手里还拿着一根木棍,名叫“哭丧棒”。《三国演义》里也有一章,《柴桑口卧龙吊丧,耒(lěi)阳县凤雏理事》,说的是赤壁之战以后,周瑜金疮迸发,不幸英年早逝,在东吴似乎大家都有一个共识,那就是周瑜是被诸葛气死的。诸葛亮为继续巩固孙刘联盟,消除误解,毅然冒险到东吴吊丧,可见吊丧之礼之重。吊丧是比较讲究的,除了繁琐的仪式外,有时还要诵读祭文,表扬一下死者,表达一下自己因死者的逝去而给自己带来的悲痛。一般老百姓文化不高,可能写不出祭文,则会一边涕泪横流,一边在口里念叨“你(指死者)让我怎么活呀?”
孔子在一日之内,哭人之丧,馀哀未息,故不歌。是以哀伤可以多保留一些时候,乐与怒不可以长久保留,此非礼制,乃人心之仁道。本章见圣人之心,即见圣人之仁。
孔子在这里又提到富贵与道的关系问题。只要合乎于道,富贵就可以去追求;不合乎于道,富贵就不能去追求。那么,他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从此处可以看到,孔子不反对做官,不反对发财,但必须符合于道,这是原则问题,孔子表明自己不会违背原则去追求富贵荣华。
《韶》乐是当时流行于贵族当中的古乐。孔子对音乐很有研究,音乐鉴赏能力也很强,他听了《韶》乐以后,在很长时间内品尝不出肉的滋味,这当然是一种形容的说法,但他欣赏古乐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,也说明了他在音乐方面的高深造诣。
三月不知肉味:《史记》作“学之三月”,谓在学时不知肉味。或说:当以闻韶三月为句。此三月中常闻韶乐,故不知肉味。
不图为乐之至于斯:孔子本好乐,闻韶乐而深美之,至于三月不知肉味,则其好之至矣。于是而叹曰:“不图为乐之移人有至此。”或说:斯字指齐,谓不图韶乐之至于齐。
今按:本章多曲解。一谓一旦偶闻美乐,何至三月不知肉味。二谓《大学》云:“心不在焉,食而不知其味。”岂圣人亦不能正心?三谓圣人之心应能不凝滞于物,岂有三月常滞在乐之理。乃多生曲解。不知此乃圣人一种艺术心情。孔子曰: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。”此亦一种艺术心情。艺术心情与道德心情交流合一,乃是圣人境界之高。读书当先就本文平直解之,再徐求其深义。不贵牵他说,逞曲解。
卫国国君辄即位后,其父与其争夺王位,这件事恰好与伯夷、叔齐两兄弟互相让位形成鲜明对照。这里,孔子赞扬伯夷、叔齐,而对卫出公父子违反等级名分极为不满。孔子对这两件事给予评价的标准就是符不符合礼。
孔子极力提倡“安贫乐道”,认为有理想、有志向的君子,不会总是为自己的吃穿住而奔波的,“饭疏食饮水,曲肱而枕之”,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,可以说是乐在其中。同时,他还提出,不符合于道的富贵荣华,他是坚决不予接受的,对待这些东西,如天上的浮云一般。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古代的知识分子,也为一般老百姓所接受。
孔子自己说,“五十而知天命”,可见他把学《易》和“知天命”联系在一起。他主张认真研究《易》,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“天命”。《史记•孔子世家》中说,孔子“读《易》,韦编三绝”。他非常喜欢读《周易》,曾把穿竹简的皮条翻断了很多次。这表明孔子活到老、学到老的刻苦钻研精神,值得后人学习。
这一章里孔子自述其心态,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”,连自己老了都觉察不出来。孔子从读书学习和各种活动中体味到无穷乐趣,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者,他不为身旁的小事而烦恼,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。
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,就是好学。这里面没有什么玄虚的事情,你要是能好学,你也能成就,这是孔子给我们示现的榜样,让我们可以学习。如果他示现一个生而知之的样子,一出生来就是天才,那我们没办法学他,那好学我们就能学。朱子讲这三句话,说发愤忘食,是讲他「未得」,就是还没有得道之前,孔子发愤忘食,这是好强、好学,努力精进,废寝忘餐。
「已得」,就是他已经得道了,得道了非常的快乐,乐以忘忧,没有忧恼。得道了之后,心里面真的没有任何的忧虑、恐惧。《大学》里面讲,「有所恐惧,则不得其正」;「有所忧患,则不得其正」。那他已经得道了,当然内心里已经没有忧患、没有恐惧、没有好乐、没有忿懥,忿懥就是愤怒。这就是心中没有贪瞋痴,离开了烦恼,他就乐。那个乐,不是世间五欲之乐,而是法喜,是脱离了烦恼之后的那个乐,所以叫乐以忘忧。这两者是通过「俛焉日有孳孳」,俛是勤勉的勉,通假字。这个「俛焉日有孳孳」,原文是出于《礼记.表记》,这是讲他孜孜不倦的、勤勉的努力在那求道。
「不知老之将至」,就是他已经把自己年岁都忘了,不知道年数之不足,年纪愈来愈大了,自己都没意识到,永远做一个求学者、做一个学生,向古圣先贤学习,真正是活到老、学到老、学不了。了,就是学完了,学着学着学不完了,所以终身在学习。这是孔老夫子自己评价自己好学之笃,笃是用功、专注。这是朱子对这三句话的解释。
在孔子的观念当中,“上智”就是“生而知之者”,但他却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。他之所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,在于他爱好古代的典章制度和文献图书,而且勤奋刻苦,思维敏捷。这是他总结自己学习与修养的主要特点。他这么说,是为了鼓励他的学生发愤努力,成为各方面的有用人才。
孔子大力提倡“仁德”、“礼治”等道德观念,从《论语》书中,很少见到孔子谈论怪异、暴力、变乱、鬼神,如他“敬鬼神而远之”等。但也不是绝对的。他偶尔谈及这些问题时,都是有条件的,有特定环境的。
此四者人所爱言。孔子语常不语怪,如木石之怪水怪山精之类。语德不语力,如荡舟扛鼎之类。语治不语乱,如易内蒸母之类。语人不语神,如神降于莘,神欲玉弁朱缨之类。力与乱,有其实,怪与神,生于惑。
三人行,其中一人是我。不曰三人居,而曰三人行,居或日常相处,行则道途偶值。何以必于两人而始得我师,因两人始有彼善于此可择,我纵不知善,两人在我前,所善自见。古代善道未昌,师道未立,群德之进,胥由于此。《孟子》曰:“舜之居深山之中,与木石居,与鹿豕游,及其闻一善言,见一善行,沛然若决江河。”《中庸》亦言:“舜善与人同,乐取于人以为善。”皆发挥此章义。
孔子之学,以人道为重,斯必学于人以为道。道必通古今而成,斯必兼学于古今人以为道。道在人身,不学于古人,不见此道之远有所自。不学于今人,不见此道之实有所在。不学于道途之人,则不见此道之大而无所不包。子贡曰:“夫子焉不学,而亦何常师之有。”可知道无不在,惟学则在己。能善学,则能自得师。
本章似孔子就眼前教人,实则孔子乃观于古今人道之实如此而举以教人。孔子之教,非曰当如此,实本于人道之本如此而立以为教。孔子曰:“性相近,习相远。”此后孟子道性善,皆本于此章所举人道之实然而推阐说之。然则孔子之创师道,亦非曰人道当有师,乃就于人道之本有师。《中庸》曰:“道不远人”,其斯之谓矣。
公元前492年,孔子从卫国去陈国时经过宋国。桓魋听说以后,带兵要去害孔子。当时孔子正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周礼的仪式,桓魋砍倒大树,而且要杀孔子,孔子连忙在学生保护下,离开了宋国,在逃跑途中,他说了这句话。他认为,自己是有仁德的人,而且是上天把仁德赋予了他,所以桓魋对他是无可奈何的。
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:
孔子去曹,适宋,与弟子习礼大树下。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,拔其树。孔子去。弟子曰:“可以速矣。”孔子曰:“天生德于予,桓魋其如予何!”
通过这件事,既体现了孔子的从容自信,又体现了孔子的机智灵活一面。即使“天生德于予”,但也不必在此坐以待毙。此自信而不迷信,持经而达变之举也。不知孔子者,有言其迂腐呆板者,可参照此章反驳之。
孔子之不迂腐呆板事件还有,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:
孔子居陈三岁,会晋楚争强,更伐陈,及吴侵陈,陈常被寇。孔子曰:“归与!归与!吾党之小子狂简,进取不忘其初。”于是孔子去陈。
过蒲,会公叔氏以蒲畔,蒲人止孔子。弟子有公良孺者,以私车五乘从孔子。其为人长贤,有勇力,谓曰:“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,今又遇难于此,命也已。吾与夫子再罹难,宁鬬(dòu,同斗)而死。” 鬬甚疾。蒲人惧(家语云:“我宁鬬死,挺剑而合觽(xī),将与之战,蒲人惧”是也),谓孔子曰:“苟毋适卫,吾出子。”与之盟,出孔子东门。孔子遂适卫。子贡曰:“盟可负邪?”孔子曰:“要盟也,神不听。”
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,是丘也:此重申上句意。孔子谓我平日无所行而不与二三子以共见。诸君所共见者,即丘其人。学于其人,其人具在,复何隐?此处孔子特地提出一行字,可谓深切之教矣。盖诸弟子疑孔子于言有隐。孔子尝曰:“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。”又曰:“天何言哉?”“予欲无言。”不知天虽无言,时行物生,天道已昭示在人,而更何隐?诸弟子不求之行而求之言,故孔子以无行而不与之道启之。
本章孔子提醒学者勿尽在言语上求高远,当从行事上求真实。有真实,始有高远。而孔子之身与道合,行与学化。其平日之一举一动,笃实光辉,表里一体,既非言辨思议所能尽,而言辨思议亦无以超其外。此孔子之学所以为圣学。孔子曰:“默而识之”,其义可思矣。
本章是孔子自语,盖当时可能有人在对孔子进行访谈,问及孔子是否对同学们留了一手,或者孔子意识到有人以为自己对学生留了一手,所以孔子对此一方面进行辟谣:“吾无隐乎尔”, 另一方面又开始对学生们进行教育“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”,突出其 “行”,而不直言“言”,体现了孔子一贯的执其两端的教学风格。
孔子的一言一行,都是落在学生眼睛里的,老师教学生,一般以言为主,如今日之课堂,然而孔子却单将“行”字拈出,盖可包含二层含义:
一、于己,我孔丘是知行合一的,我所行即我所言,实践证明,我把教给你们的知识自己也在执行;
二、于人,提醒同学们不要老是在在言语上求高远,而应当从行事上求真实。有真实,始有高远。所谓说的好听,不如做的好看。
读本章可体会到孔子对于己所倡导之理念,身体力行,身与道合,行与学化。其平日之一举一动,笃实光辉,表里一体,非言辨思议所能尽,而言辨思议亦无以超其外。孔子曰:“默而识之”,其义可思矣。
本章主要讲孔子教学的内容。当然,这仅是他教学内容的一部分,并不包括全部内容。孔子注重历代古籍、文献资料的学习,但仅有书本知识还不够,还要重视社会实践活动,所以,从《论语》书中,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经常带领他的学生周游列国,一方面向各国统治者进行游说,一方面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。但书本知识和实践活动仍不够,还要养成忠、信的德行,即对待别人的忠心和与人交际的信实。概括起来讲,就是书本知识,社会实践和道德修养三个方面。
对于春秋末期社会“礼崩乐坏”的状况,孔子似乎感到一种绝望,因为他认为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,难以找到他观念中的“圣人”、“善人”,而那些“虚而为盈,约而为泰”的人却比比皆是,在这样的情况下,能看到“君子”、“有恒者”,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其实,只用有一个鱼钩的钓竿钓鱼和用网捕鱼,和只用箭射飞行中的鸟与射巢中之鸟从实质上并无区别。孔子的这种做法,只不过表白他自己的仁德之心罢了。
本章里,孔子提出对自己所不知的东西,应该多闻、多见,努力学习,反对那种本来什么都不懂,却在那里凭空创造的做法。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,同时也要求他的学生这样去做。
孔子时常向各地的人们宣传他的思想主张。但在互乡这个地方,就有些行不通了。所以他说:“与其进也,不与其退也”;“人洁己以进,与其洁也,不保其往也”,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孔子“诲人不倦”的态度,而且他认为不应死抓着过去的错误不放。
从本章孔子的言论来看,仁是人天生的本性,因此为仁就全靠自身的努力,不能依靠外界的力量,“我欲仁,斯仁至矣。”这种认识的基础,仍然是靠道德的自觉,要经过不懈的努力,就有可能达到仁。这里,孔子强调了人进行道德修养的主观能动性,有其重要意义。
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夫人,违反了礼的规定,而孔子却说他懂礼。这表明孔子的确在为鲁昭公袒护,即“为尊者讳”。孔子以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为最高原则,所以他自身出现了矛盾。在这种情况下,孔子又不得不自嘲似地说,“丘也幸,苟有过,人必知之。”事实上,他已经承认偏袒鲁昭公是自己的过错,只是无法解决这个矛盾而已。
可能孔子所和与人歌所歌不同,而是孔子根据人歌的题材、格律,另外唱一首歌。
孔子其实很有情趣,可能还不能称作一个歌唱家,但至少会欣赏,并很会赞赏别人,试想,你如果唱的好,孔子让你再唱一遍,然后他再根据你所唱的歌的题材、格律,他再唱上一首,你是何等感觉,这岂不是一个非常和乐的场景。
对于“文,莫吾犹人也”一句,在学术界还有不同解释。有的说此句意为:“讲到书本知识我不如别人”;有的说此句应为:“勤勉我是能和别人相比的。”我们这里采用了“大约我和别人差不多”这样的解释。他从事教育,既要给学生传授书本知识,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。他说自己在身体力行方面,还没有取得君子的成就,希望自己和学生们尽可能地从这个方面再作努力。
本篇第2章里,孔子已经谈到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,本章又说到“为之不厌,诲人不倦”的问题,其实是一致。他感到,说起圣与仁,他自己还不敢当,但朝这个方向努力,他会不厌其烦地去做,而同时,他也不感疲倦地教诲别人。这是他的由衷之言。仁与不仁,其基础在于好学不好学,而学又不能停留在口头上,重在能行。所以学而不厌,为之不厌,是相互关联、基本一致的。
孔子患了重病,子路为他祈祷,孔子对此举并不加以反对,而且说自己已经祈祷很久了。对于这段文字怎么理解?有人认为,孔子本人也向鬼神祈祷,说明他是一个非常迷信天地神灵的人;也有人说,他已经向鬼神祈祷很久了,但病情却未见好转,表明他对鬼神抱有怀疑态度,说孔子认为自己平素言行并无过错,所以祈祷对他无所谓。这两种观点,请读者自己去仔细品评。
春秋时代各诸侯、大夫等都极为奢侈豪华,他们的生活享乐标准和礼仪规模都与周天子没有区别,这在孔子看来,都是越礼、违礼的行为。尽管节俭就会让人感到寒酸,但与其越礼,则宁可寒酸,以维护礼的尊严。
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是自古以来人们所熟知的一句名言。许多人常常将此写成条幅,悬于室中,以激励自己。孔子认为,作为君子,应当有宽广的胸怀,可以容忍别人,容纳各种事件,不计个人利害得失。心胸狭窄,与人为难、与己为难,时常忧愁,局促不安,就不可能成为君子。
这是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赞扬。孔子认为人有各种欲与情,这是顺因自然的,但人所有的情感与欲求,都必须合乎“中和”的原则。“厉”、“猛”等都有些“过”,而“不及”同样是不可取的。孔子的这些情感与实际表现,可以说正是符合中庸原则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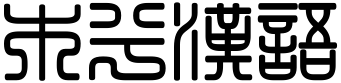
本篇共包括38章,也是学者们在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时引述较多的篇章之一。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:“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”;“饭疏食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在其中”;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;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;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;“温而厉,威而不猛,恭而安。”本章提出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学习态度,孔子对仁德等重要道德范畴的进一步阐释,以及孔子的其他思想主张。
本章孔子论用行舍藏,有道亦复有命。如怀道不见用是命。行军不能必胜无败,亦有命。文中虽未提及命道二字,然不参入此二字作解,便不能得此章之深旨。读《论语》,贵能逐章分读,又贵能通体合读,反复沉潜、交互相发,而后各章之义旨,始可透悉无遗。
孔子在本章提出不与“暴虎冯河,死而无悔”的人在一起去统帅军队。因为在他看来,这种人虽然视死如归,但有勇无谋,是不能成就大事的。“勇”是孔子道德范畴中的一个德目,但勇不是蛮干,而是“临事而惧,好谋而成”的人,这种人智勇兼有,符合“勇”的规定。